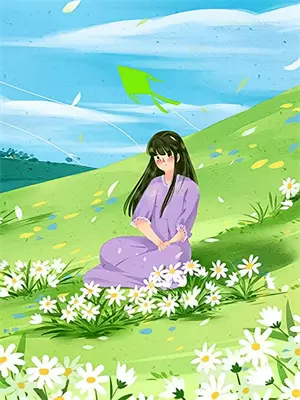- 青痕锁玉匣,梅熟透帘霜(苏曼琳苏曼琳)免费阅读_完结热门小说青痕锁玉匣,梅熟透帘霜(苏曼琳苏曼琳)
- 分类: 言情小说
- 作者:凡尘净土心无痕
- 更新:2025-07-23 12:55:46
《青痕锁玉匣,梅熟透帘霜(苏曼琳苏曼琳)免费阅读_完结热门小说青痕锁玉匣,梅熟透帘霜(苏曼琳苏曼琳)》精彩片段
江南的梅雨天,墙根长出了薄而凉的青苔。弄堂里积水的砖缝倒映着灰白天空的碎影。
李阿婆从窗子里探出身来喊小孙子回家,声音像浸了水的棉线,在湿漉漉的雾气里一扯便断。
苏曼琳斜倚在自家小阳台的木质栏杆上,指尖冰凉。
楼下灶坡间飘上来一丝若有若无的萝卜糕焦香气,是隔壁周师母的手笔,用料俭省,
香气也便单薄。她的目光越过无数灰黑参差的屋顶,
停留在对面三楼那扇未曾拉开过的墨绿色窗帘上。自从陈先生全家迁去香港,
那窗就像一只永远阖上的眼睛。窗台角落里,残留着一只豁了口的白瓷盆,
盆里枯败的几茎草叶如同被遗忘的线头。
笑声、甚至黄昏时陈先生破旧留声机里淌出来的《夜上海》……都被这细密连绵的雨浸透了,
消了形迹。苏曼琳下意识地抚了抚左手腕,那里空荡荡的,
只留下一点比肤色更浅淡的圆痕——母亲临终前压箱底的那只糯玉镯子,
上月已悄然进了永安当铺幽深的木柜台格子,换成了手里这几张轻薄的法币。
指腹碾过崭新的纸边,一种钝涩的陌生感。楼梯吱嘎一响,阿秀端着粗瓷碗碟上来。
碗里盛着清可见底的薄粥,碟子上仅有两小块腐乳,边缘染了些许陈年黑渍。阿秀动作麻利,
眼睛只在主家腕上那点褪色的痕迹停了一瞬,便垂了下去,嘴唇无声地抿成一条直线。
她摆好碗碟,刚挪步,却又被苏曼琳叫住。“这萝卜糕的火候,”苏曼琳声音不高,
穿过淅淅沥沥的雨幕送过去,像给湿绒布擦过一遍,“周师母今年又舍得放足了料么?
”她话尾飘在空气里,不知是问阿秀,还是问隔邻那紧闭的窗。阿秀步子顿住,
微微侧了侧脸。她常年浸在油烟里的面庞没有什么波澜:“她呀,还是老规矩。
白萝卜切得丝儿粗些,虾米碎也只撒那么一小撮,油么……就更省啦。倒是夸讲了几遍,
讲小姐有双识货的眼睛,如今家里那套细瓷碗盏,还是从前在您母亲手里转来的旧物,
光亮得很……”细密雨脚敲打着阳台遮檐下生锈的铁皮,“噼啪”声被放大许多倍。
苏曼琳的指腹无意识地在那粗粝的栏杆上反复摩挲,直到一丝木刺扎入指尖,微痛,粘腻。
对面那扇墨绿窗幔依旧沉默。她看着粥上漂浮的、过于细小的腐乳块,
在昏暗天色里也红得刺目。再省俭的心思,
也拦不住物价日日爬高的腿——楼下灶坡间飘来的萝卜糕气息,淡得几乎只剩一缕水汽。
人世的体面,原也不过是浮在生活这碗薄粥上的一星油花罢了。天是彻底塌不透的,
总留有一线缝。转过年关了,冷空气劈头盖脸砸下来,上海滩的冬天凛冽如刀。
苏曼琳走进亨昌公司那间小小的账房时,鼻尖还冻得微红。
她把收在旧羊皮手提袋里、仔细熨烫平整的履历递过去,深蓝色卡其布旗袍领口浆得挺括,
领襻锁着一小粒温润无光的珠扣。负责的刘先生抬眼只扫了一瞥,
搁在桌边的热水杯在他抬手时撞倒,洒出的水迅速洇湿了小半页纸。“苏小姐,
”刘先生草草拿起那湿漉的纸角,语气像是念一个无关紧要的脚注,“做本票贴现登记的。
字总要写得快,写得好——字要清正端方,要紧的是快。
”他随手抓过一张空白票样推到她眼前,“试一张看看?”账房里没有炉子,
寒气从砖缝里、木窗隙里丝丝钻入。苏曼琳冻得微僵的手指,握紧那支磨得滑亮的蘸水笔,
笔尖划过劣质票据的粗糙表面,带起沙沙的声响。墨水洇开得很快,
字迹边缘就有些模糊的毛边。她写得不快,但笔画勾勒清晰,
一撇一捺均显出早年临帖留下的风骨。“苏”字的“口”部,最后一横因手腕微颤,
到底留了个不甚圆润的小顿点。刘先生枯瘦的手指在票面上一敲:“不行啊,
”那“口”字上的墨点如同被打落的蛾子,“太慢了。我们这里每日过手的票据,
像潮水一样的。”他不再看她,“下一位。”只三个字,像小石子投入冷彻的空气,
连多余的回声也发不出。苏曼琳无声地收起那墨迹未干的票样,指尖捻过湿润的纸面,
一片冰凉,墨迹化开些许沾染在指腹上,一点乌青的印记,像甩不脱的尴尬。
她走出亨昌公司那扇油得发亮的沉重玻璃门,门轴上缺油的吱呀声很响。
斜对街“徐记”那红底金字的招幌在西北风里簌簌颤抖,刚出炉的生煎包子香气浓烈霸道,
裹着油煎的喧腾气味撞入她的鼻腔。一个黄包车夫蹲在店铺屋檐下,
粗糙的手指捏着焦黄酥脆的包子底,烫得直吹气,浓油浸润的汁水顺着指缝滴落。
他大口吞咽,脸上每一道深深的褶痕都写着对这滚烫油香最虔诚的满足。
苏曼琳把冻得冰凉的、印着墨痕的手指插入大衣口袋深处,
那半页洇湿的无用履历硌着口袋衬布。她加快了步子,高跟鞋敲在冻结的人行道上,一下,
又一下,急急地。暮春三月,邮差的绿车子停在弄堂口。一个厚重的牛皮纸信封,
带着异国的油墨气息,躺在苏曼琳手心。拆开,一张彩色相片滑了出来,
背面贴着一张花哨的香港邮票。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时兴的低领洋装,鲜亮的柠檬黄。
颈间坠着一条沉甸甸的金链子,镶了钻,即使在印制的相纸上,也折射出不容错认的光芒。
她亲昵地挽着一个穿笔挺格纹西装男人的手臂,背景是维多利亚港绚丽的夜色灯火,
水面上霓虹倒影如流淌的琉璃碎片,闪得人眼花。
一行竖排钢笔字在相片空白处:“曼琳妹雅存。惜妹未同行,惟见香江璀璨。顺问沪上寒暖。
若清 书于港岛”。苏曼琳捏着这张纸片,走到自家天井狭窄的天空下,抬头望去。
傍晚的天空没有璀璨灯火,只有一抹惨淡的褪色夕阳,晕染在洗得发白的小块蓝天里。
石库门高耸的墙垣切碎了这方寸的蓝色。鼻尖飘来隔壁灶间炸菜的油烟,浓烈地呛人。
是油不够旺,青菜与盐同炒,生涩的菜气盖住了本该有的油香,
徒留一股纠缠不清的烟火浊气在弄堂的夹缝中弥散。她把照片随手放在窗边五斗橱上,
挨着那瓶蔫头耷脑、边缘泛黄的野菊。花是上个月生日时弄堂里几个相熟的妇人送来的,
从城郊野地里采来。阿秀拿玻璃瓶养着,勤换水,也终于要熬到尽头了。
照片上那片富丽的柠檬黄和满纸的港岛光华,
就在这陋室斑驳墙纸、水渍晕开的角落里兀自亮着,亮得像一种刻薄的反光板。
阿秀端着饭碗进来,瞟了一眼那花哨的相片,又望了望那瓶苟延残喘的野菊花,没作声。
她将一碟新炒好的冬笋片搁在桌上,热气腾腾。寻常的土黄色,笋片边缘略焦,
带着锅气的微脆和本味的清甜爽口。苏曼琳拿起碗筷。筷子头夹起一片冬笋,牙齿咬下去,
“喀哧”一声轻响,平淡日子里一种实在的慰藉。
弄堂口那颗歪斜的老梧桐叶子掉得差不多了,冬日的寒气钻骨入髓。阿秀病了两天,
咳得整晚整晚如风箱破洞,实在捱不过。苏曼琳只得穿起阿秀平日里那件深蓝粗布围兜,
去老虎灶打热水回来烧洗用。水还没开,炉膛上那只旧铜壶沉闷地发出“嗡嗡”低响。
苏曼琳弯腰,用铁钳拨弄着炉子里半燃的煤球。烟带着一股刺鼻的硫黄味猛地倒灌出来,
她被呛得闭了眼,强忍住一阵剧烈的呛咳,眼泪生生逼了出来。粗硬的木柴枝擦过脸颊,
带下一道细不可见的灰痕。冰冷的自来水从盆里舀出,浇在布满陈年油垢的灶台表面,
需要她挽起袖口,用刷子费力地擦洗。水溅在粗布围兜上,迅速洇开一大片深色湿痕,
寒意在衣料上贴着皮肤蔓延开,刺骨。她低头看着自己浸在冰凉皂水里的手,
纤瘦的指骨被水泡得发白发皱。这是写不赢票据的手,也是沾满灶油的手。
指关节传来微微的酸胀感。她抬手抹了下额角渗出的薄汗,袖口扫过炉灶边缘的黑灰,
蹭上了眉梢也未觉察。灶膛里的火苗终于舔舐上铜壶底,发出“滋滋”的水响预热声。
冬日下午惨淡的天光从灶坡间上方的小窗泻入,斜斜的一道光,
照着漂浮在粗陶盆水面上的皂泡,闪动微弱的虹彩,转眼即逝。
苏曼琳的目光停在窗边木架子上。一只墨绿色的旧玻璃瓶里,清水中养着的几株野水仙,
是她前日从小菜场角落买回的便宜货。洁白花瓣包裹着鹅黄蕊心,
在这烟气油腻、光线昏暗的灶间角落,静静吐露着清逸的甜香。那香气并不浓郁,
却执着地萦绕在她每次吸气的瞬间,像某种微不可闻却始终存在的和弦。
同类推荐
 闺蜜偷我精神气组团出道玖日姜雪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全集免费小说闺蜜偷我精神气组团出道玖日姜雪
闺蜜偷我精神气组团出道玖日姜雪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全集免费小说闺蜜偷我精神气组团出道玖日姜雪
玖日故事
 刑部尚赵怀德《状元揭榜遭举报祖父拥兵造反》完结版免费阅读_刑部尚赵怀德热门小说
刑部尚赵怀德《状元揭榜遭举报祖父拥兵造反》完结版免费阅读_刑部尚赵怀德热门小说
玖日故事
 害我名声尽毁后,他求我高抬贵手(顾惜染许承安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害我名声尽毁后,他求我高抬贵手(顾惜染许承安)
害我名声尽毁后,他求我高抬贵手(顾惜染许承安)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害我名声尽毁后,他求我高抬贵手(顾惜染许承安)
糯米团团
 宋祈悦傅淮一《闲翻旧卷岁月淮》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《闲翻旧卷岁月淮》全本在线阅读
宋祈悦傅淮一《闲翻旧卷岁月淮》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《闲翻旧卷岁月淮》全本在线阅读
叁楂有糖
 凄凄不怯怯宋逸沈梨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看凄凄不怯怯宋逸沈梨
凄凄不怯怯宋逸沈梨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看凄凄不怯怯宋逸沈梨
金流
 草长飞鸢上碧霄(萧渊沈曼青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草长飞鸢上碧霄(萧渊沈曼青)
草长飞鸢上碧霄(萧渊沈曼青)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草长飞鸢上碧霄(萧渊沈曼青)
酸辣糖果
 夫君当首辅后逼我喝下毒酒霍凛谢景明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夫君当首辅后逼我喝下毒酒霍凛谢景明
夫君当首辅后逼我喝下毒酒霍凛谢景明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夫君当首辅后逼我喝下毒酒霍凛谢景明
书信
 父亲带私生子抢遗产(蛋挞君顾墨)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父亲带私生子抢遗产(蛋挞君顾墨)
父亲带私生子抢遗产(蛋挞君顾墨)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父亲带私生子抢遗产(蛋挞君顾墨)
蛋挞君
 又见珠玉锦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又见珠玉锦秀(珠玉侯爷)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
又见珠玉锦秀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又见珠玉锦秀(珠玉侯爷)小说免费阅读大结局
黑岩家的二两桂花
 新婚夜,老公要和我AA份子钱无事陈俊最新完本小说_免费小说大全新婚夜,老公要和我AA份子钱(无事陈俊)
新婚夜,老公要和我AA份子钱无事陈俊最新完本小说_免费小说大全新婚夜,老公要和我AA份子钱(无事陈俊)
无事小神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