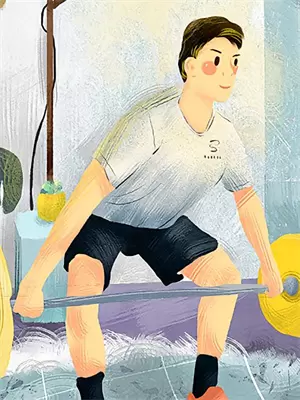
- 成神300年一种冰冷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成神300年(一种冰冷)
- 分类: 穿越重生
- 作者:肥猪大王
- 更新:2025-07-22 14:34:12
《成神300年一种冰冷热门的网络小说_完整版小说成神300年(一种冰冷)》精彩片段
登神那日,我剥离凡心,独坐云端神殿。儿子却选择留在凡间,沉迷草药与医术。三百年后,
他垂垂老矣,捧着草药来神域告别。“爹,您追逐天道永恒,我只偏爱人间刹那。
”他化作星尘消散时,我收回了延寿的神力。神座冰冷刺骨,我才懂得永恒的真相是孤独。
直到某天,神殿角落竟长出儿子当年带来的草药。原来凡人早已用另一种方式,抵达了不朽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云海在我脚下翻涌,
如同凝固的、无声的滔天巨浪,托举着这座新生的神殿。星辰悬垂,近得仿佛伸手可摘,
那些冰冷而永恒的光点,是神座周围最寻常的点缀。此处无风,无尘,
亦无凡俗意义上的时间流淌。唯有浩瀚磅礴的神力在殿宇的玉柱金梁间无声脉动,
每一次轻微的震荡,都呼应着寰宇深处某个星辰的诞生或寂灭。我,林玄,
端坐于这冰冷的星辰神座之上。刚刚剥离凡心的余痛,像是一道深可见骨的创口,
虽不再流血,却依旧隐隐牵扯着神魂的深处。那是一种奇异的空茫,
曾经牵动肺腑的爱恨悲欢,如今望去,竟如隔着万丈冰层观看水底模糊的游鱼,色彩褪尽,
只余下轮廓与影。这便是代价,
换取这俯瞰万古、执掌星辰伟力的冰冷神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我缓缓抬起手,
指尖萦绕着一缕纯粹的星辉,它温顺地流淌,
蕴含着足以轻易重塑山河或焚毁星辰的恐怖意志。力量,无边无际的力量,如渊如海,
充塞四肢百骸,也填满了那剥离凡心后留下的巨大空洞。
就在指尖的星辉流转至最璀璨的一刻,一股截然不同的、极其细微却无比清晰的悸动,
猛地刺穿了神躯深处!它并非源于浩瀚神力,而是来自血脉最深处那根从未真正断绝的丝弦。
这悸动如此微弱,却又如此熟悉,带着一种行将彻底消散的枯竭意味,
像一盏在无边寒夜中即将燃尽最后灯油的烛火。林修!这个名字,
带着三百年前凡尘泥土的气息与炉火的温暖,猝不及防地撞开了神殿冰冷的寂静。
星辰神座散发出的永恒光辉似乎都为之微微一滞。我霍然抬首,神念如无形的狂澜,
瞬间撕裂了层层叠叠的云障,穿透了广袤无垠的大地,
精准地落向那片我早已远离、却又从未真正遗忘的故土——青岚山下,
那座依着潺潺溪流而建的简朴院落。神念所及,景象纤毫毕现。小小的庭院依旧整洁,
晒药架上陈列着各色风干的草叶根茎,在凡间的日光下散发着微苦而熟悉的芬芳。石桌旁,
一个身影佝偻着,正低头专注地碾磨着石臼中的药材。白发稀疏,如同深秋覆着薄霜的衰草,
枯瘦的双手布满深褐色的老人斑,动作缓慢而吃力,
每一次石杵的落下都带着一种令人心颤的滞涩。他时不时停下,剧烈地咳嗽,
那撕心裂肺的声响仿佛要将这副枯槁的躯壳彻底震碎,单薄的肩膀随之剧烈起伏,
如同狂风中断了线的残破风筝。生命的气息,在他身上已稀薄如风中残烛,摇曳着,
随时可能熄灭。这便是我的儿子,林修。
那个曾经在春日山野间奔跑欢笑、眼神明亮如星辰的少年,
那个固执地拒绝了我为他铺就的通天仙途、痴迷于草药方寸之间的孩子。三百年光阴,
于我只是神座前一次稍长的凝思,于他,却已耗尽了一生的长度。
心口那道剥离凡心留下的无形创口,毫无预兆地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,远比剥离时更甚。
神躯坚不可摧,此刻却因这源自血脉的、凡俗生命的枯竭而微微震颤。
指间流转的星辉骤然失控,化作几道凌厉的光束激射而出,无声地湮灭在神殿边缘的虚空里。
冰冷的星辰神座上,第一次清晰地映照出一个父亲的身影,那身影深处,
翻涌着名为“痛”的惊涛骇浪。意念微动,神殿内浩瀚的云海骤然向两旁排开,
露出一条直通凡间的无形路径。空间的距离在神力面前失去了意义,一步踏出,
脚下已是凡尘的青石小径。院门“吱呀”一声轻响,惊动了石桌旁专注的身影。
林修猛地抬起头。浑浊的眼珠在看清我的瞬间,爆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光彩,
仿佛干涸的河床深处突然涌出清泉。那光芒短暂地驱散了死亡的灰败,
让那张布满沟壑的脸庞瞬间生动起来。他下意识地想站起身,
动作却因身体的极度虚弱而显得笨拙踉跄。“爹!”一声呼唤,沙哑、干涩,
带着剧烈的喘息,却蕴含着跨越了三百年光阴的孺慕与激动。这声音撞在神殿冰冷的玉壁上,
仿佛能激起微弱的回响。我疾步上前,神力本能地在指尖凝聚,化作一股温润柔和的暖流,
无声无息地渡入他枯槁的身体。那暖流如同生命之泉,滋养着他行将枯竭的经脉,
强行挽留着那如游丝般的气息。他急促的喘息肉眼可见地平复下来,
脸上不正常的潮红也褪去少许。
“爹…您怎么…”他看着我身上流转的星辉神纹和那不属于凡尘的威仪,眼中是纯粹的欣喜,
并无丝毫面对神灵的畏惧,“您真的…成了…”“跟我走,修儿。
”我的声音在神力的加持下显得平静无波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,“神域之中,
自有续命长生之法。这点凡尘寿元的枯竭,并非绝路。
”我的目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和枯瘦的手上,那景象比任何神魔大战的伤口更刺目。
林修却缓缓地、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他吃力地抬起手,指向石桌旁一个半旧的粗布包裹,
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孩童般执拗的神情:“不急,爹…您先看看这个。”他颤抖着手,
一层层解开那包裹。里面并非什么珍奇仙草,而是一株株形态各异的寻常植物,
根须上甚至还沾着新鲜的泥土。每一株都被小心地用湿润的苔藓包裹着。
“这…是‘七星伴月草’,长在峭壁背阴处,
我找了七年才寻到这么几株…您看它叶底的星点,只有在月圆后三天的晨露未干时才最清晰,
药性也最好…”他枯瘦的手指珍爱地抚过一株叶片边缘带着锯齿的青色小草,
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专注而满足的光,“用它配上三年前采的‘雾隐花’根须,
老张头那折磨了他半辈子的腿寒,
入冬再没犯过…”他又拿起一株开着不起眼小白花的藤蔓:“这个…‘绕指柔’,最难伺候,
非得长在溪流拐弯、水声最响的石缝里…但它能解‘赤火蝎’的毒,快得很!
山那边寨子里猎户老李家的娃,去年被蛰了,眼看没气儿,
就是靠它抢回来的…”他的声音断断续续,夹杂着压抑不住的咳嗽,
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热情。每一株草,每一朵花,在他口中都承载着一段故事,
一个被挽救的生命,一个被驱散的病痛。他如数家珍,仿佛那是他一生最珍贵的宝藏。“爹,
您看,”他小心翼翼地托起一片形状奇特的深紫色叶子,
叶脉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银线,“这是‘紫绶衣’,我琢磨了**十年,
才勉强弄清了它止血生肌的脾气。前年山崩,压伤了好些人,伤口深得见骨,
用它捣烂了敷上,再重的伤,只要一口气在,都能吊住命,
给大夫留出救命的时间…王木匠家的小孙子,那么小的人儿,腿都快压烂了…现在,
能跑能跳了…”他浑浊的眼中泛起一丝微光,嘴角费力地向上扯动,
那是一个属于医者的、纯粹的笑容。我沉默地听着。指尖凝聚的、足以逆转生死的神力光芒,
不知何时已悄然黯淡下去。神念笼罩下,我能清晰地“看”到,
随着他讲述这些草药和它们治愈的故事,他体内那原本微弱如风中残烛的生命之火,
竟奇异地稳定了片刻,甚至微弱地明亮了一丝。那并非神力强行灌注的结果,
而是源于他灵魂深处燃烧不息的、对脚下这片土地和其上生命的热爱与执着。
三百年前那个暴雨倾盆的黄昏,骤然浮现在眼前。
豆大的雨点砸得药圃里新栽的幼苗东倒西歪,泥水四溅。刚刚十几岁的林修,
瘦小的身影在暴雨中拼命地用身体护住那些脆弱的药苗,蓑衣早已湿透贴在身上,小脸煞白,
嘴唇冻得发紫,却固执地不肯回屋。雨水顺着他紧抿的嘴角流下,混合着倔强的泪水。“爹!
它们会死的!”他朝站在廊下的我嘶喊,声音淹没在雷声里。我那时已初窥元婴门径,
心念微动,一层无形的灵力屏障瞬间笼罩了整个药圃,风雨立止,
倒伏的幼苗在柔和的光晕中迅速挺立、舒展,恢复勃勃生机。“好了,回屋吧。
”我的声音平静无波。他却猛地摇头,冲到那些被灵力复原的幼苗旁,
固执地伸出满是泥泞的手,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幼苗扶正,重新培上被雨水冲散的泥土。
他的动作笨拙而认真,指尖被碎石划破也浑然不觉。“不一样的,爹…”他低着头,
声音闷闷的,带着哭腔,“您让它们活了…可它们没经过这场雨…根没扎稳…下一次风来,
还是会倒的…我得自己把它们种好…”少年眼中那种近乎固执的坚持,
与此刻眼前老者抚摸草药时眼中跳跃的光芒,跨越三百年的时光,完美地重合在一起。
同类推荐
 第四章:蛆虫时钟陈墨李国强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第四章:蛆虫时钟(陈墨李国强)
第四章:蛆虫时钟陈墨李国强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第四章:蛆虫时钟(陈墨李国强)
佚名
 第三章:双排扣西装陈墨周昊免费小说全集_小说免费完结第三章:双排扣西装陈墨周昊
第三章:双排扣西装陈墨周昊免费小说全集_小说免费完结第三章:双排扣西装陈墨周昊
佚名
 第二章:质谱谜题陈墨周昊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第二章:质谱谜题陈墨周昊
第二章:质谱谜题陈墨周昊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第二章:质谱谜题陈墨周昊
佚名
 第一章:尸斑王建国张德顺完整版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第一章:尸斑(王建国张德顺)
第一章:尸斑王建国张德顺完整版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第一章:尸斑(王建国张德顺)
佚名
 执杖纵红尘(李淳阮名)热门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在线看执杖纵红尘李淳阮名
执杖纵红尘(李淳阮名)热门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在线看执杖纵红尘李淳阮名
开薪
 执杖纵红尘李淳阮名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执杖纵红尘(李淳阮名)
执杖纵红尘李淳阮名小说完结_免费小说全本执杖纵红尘(李淳阮名)
开薪
 李淳阮名(执杖纵红尘)全章节在线阅读_(执杖纵红尘)全本在线阅读
李淳阮名(执杖纵红尘)全章节在线阅读_(执杖纵红尘)全本在线阅读
开薪
 回旋裂缝(抖音热门)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_最新小说回旋裂缝(抖音热门)
回旋裂缝(抖音热门)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_最新小说回旋裂缝(抖音热门)
佚名
 第二章小满记与朋友圈风暴程橙苏小满完整免费小说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第二章小满记与朋友圈风暴程橙苏小满
第二章小满记与朋友圈风暴程橙苏小满完整免费小说_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第二章小满记与朋友圈风暴程橙苏小满
佚名
 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(苏小满程橙)最新章节列表_苏小满程橙)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(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)
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(苏小满程橙)最新章节列表_苏小满程橙)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(第一章307宿舍的万能胶水)
佚名







